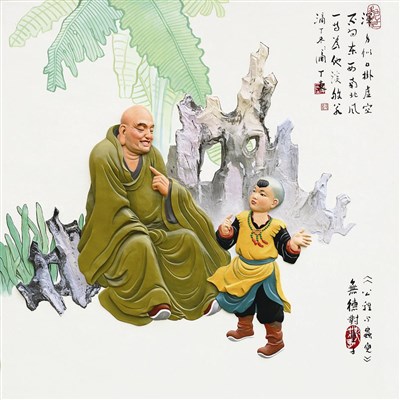《人間福報》是一份多元化的報紙,強調內容溫馨、健康、益智、環保,不八卦、不加料、不阿諛,希冀藉由優質的內涵,體貼大眾身心靈的需要,是一份承擔社會責任的報紙。
我不是「呷教」的和尚 上
字級







「呷教」,台灣話,意思是「吃教」。
台灣才光復的時候,由於過去大家在日本人的統治壓制之下,生活清苦;有一些宗教就趁機會給你一些奶粉,給你一些衣服等日常用品,但是你要來信仰他的教。大家為了要生活吃飯,就改變了信仰。所以就有人說,這許多人都是「呷教」(吃教)的。
呷教,就是靠佛教吃飯。
自我懂得佛教以後,我就希望佛教靠我,我不要靠佛教。六十六年前(一九四九年),塵空法師從浙江省普陀山託煮雲法師帶給我一封信,上面寫著:「現在我們佛教青年,要讓『佛教靠我』,不要有『我靠佛教』的想法……」,他的這封信,洋洋灑灑寫了數千言。
其實,我和塵空法師並無太多的關係,只是一九四七年(民國三十六年)在焦山的第一屆中國佛教會務人員訓練班中,他是老師,我是學生,我們僅有一面之緣而已。但是「佛教靠我」這句話,一向以來成為我心中的一盞明燈,經常這樣充電,甚至發光,增加了我的信心力量。
我出身家貧,童年七、八歲的時候,在家裡靠父母吃飯,我就想要去做童工,賺錢貼補家用。後來,我清晨起來揀狗屎,傍晚出門拾牛糞,把它堆積起來可以作肥料,賣一點錢,大人很高興,我自己也很開心。
報答恩惠 為教貢獻所有
出家以後,佛教養我、教我,所以受到打罵委屈,我都不計較。因為,我白吃了寺中的米飯,還能不受教嗎?在南京棲霞,在鎮江金山、焦山,在常州天寧等多處參學,受春風、夏雨、秋霜、冬雪的教育中,我默默的學習、靜靜的長大,總想著:如何報答佛教的恩惠,我不能長期的靠佛教吃飯,我應該對佛教有所貢獻……,這是我從小養成的觀念。
我曾說過,自許做一個報恩的人,並且發願:我要給人,不希望人家給我。所以師父志開上人「半碗鹹菜」的恩德,讓我立下弘法利生的志願,這就是我的本性。
到台灣來之前,十年叢林寺院關閉的參學生活,我幾乎每年都做飯頭(煮飯菜)、菜頭、水頭(擔水)等等苦行工作,這許多事不一定是我應該做的,但我自願發心承擔。我不曾休息過一天,自覺有一點特長,那就是煮飯菜供養大眾。其實,最初出家,我也沒有什麼志願,只想做一個飯頭和尚而已,並不想做一個人家說的「大師」,我覺得做飯頭僧可能是我人生最大的享受。
度過十年的寺院生活之後,有一個機會,我回到祖庭宜興大覺寺。這也是一個貧窮清苦的寺院,寺中有一片農場,我原本就是農家子弟,可以務農為生;寺院的附近有一所小學,我也很幸運的在裡面教書。我想,我做一個出家人,也要有所生產,在社會上,才不會被人譏為是社會的寄生蟲,也才不會給人批評是社會的消費分子。我不要靠佛教吃飯,甚至也不靠社會來救濟我,我要自力更生、自食其力。
不知道是什麼因緣,讓我從飯頭僧苦行的工作,流浪到台灣來;台灣人的善良、台灣的水米,養育我成長,甚至他們把我當作法師,要我講經說法。我最初想,所謂「是法平等,無有高下」,講經說法,與煮飯、燒菜供養大眾也是一樣,也就沒有怎麼去分別它,而漸漸走上弘法建寺、安僧度眾的道路。坦白說,現在九十歲了,你問我有什麼懊悔的事?那就是我不能做到最初想做的飯頭僧。
服務度眾 不做焦芽敗種
回想初到台灣的時候,我在中壢圓光寺做「水頭」,每天打六百桶的水供應全寺八十人使用;清晨天未亮,就拉車購買常住需要的物品,寺裡的掃地、淨頭、挑擔、收租穀、看守山林等行單,我從來沒有推辭過。我想,寺裡大眾對外省來的青年僧侶,應該會有一點好感吧!我自許要有供養心,幫忙人家吃飯,並不希望別人來幫助我。想來,服務大眾的人生觀就不會辜負自己的一生。
我也曾經想過,我既然出家,就要修行,我既要讀書,就要有讀書的環境;但我忽然感到,我也沒有錢,也沒有地,我要如何閉關修行呢?誰來給我地方呢?誰來給我吃飯呢?假如我要讀書,誰給我讀書的環境呢?
那個時候,也有寺院的護法信徒,說要護持我閉關,讓我專心寫作文章;我也曾有過念頭到靈巖山念佛一生,我也甘願在禪堂裡面打坐終老;但我覺得,假如我閉關修行有成,到了西方極樂世界、東方琉璃世界,那許多供養我的人、給我吃飯的人還在娑婆世界,他們怎麼辦呢?
想一想,這還是自私自利的行為,不能利益大眾,就打消了這種不為別人著想、只為自我成功的念頭。融齋法師曾經開示我:「未成佛道,先發心度眾,是菩薩發心。」因此,我發願要做一個菩薩;芝峰法師的一句「不要做焦芽敗種」,也讓我謹記在心,我不要做佛教的焦芽敗種。
人身可貴 不能輕慢虛度
我也有個性格,歡喜在山林裡爬上爬下的活動,享受那種遺世獨居的超然,與天地同的清淨逍遙;住在山裡面修行,沒有他事,除了早晚殿堂課誦以外,可以說自由自在,也是很愜意。但是我想到,到世間上來,只在山林裡自我修行,不能為社會服務,那來到世間上有何意義呢?只住在山林裡面,這不是消費世間嗎?不能貢獻世間,我何必做世間的廢人呢?
在佛教裡面,不少的人靠趕經懺替人念經收取一些嚫錢(紅包)為生,因為講經不容易,念經比較簡單,無所用心就可以獲得供養來養活自己。在那個生存不易的大時代,就是我去念經,也還是靠佛吃飯;加上我五音不全,念經就更不是我本來志願要走的道路了。我想到,人的生命是很可貴的,父母生養了我,讓我有機會在世間上做人,要這麼樣輕易的放過自己的人生嗎?
我也看過很多無所事事的出家人,到處雲遊行腳,我不知道他們的旅費是從哪裡來的?我也不知道他們這樣走來走去,究竟是為了什麼?我當然也想去旅遊參學、擴大見識,但我不能只是要人來幫忙我,他出錢,我去遊玩?這樣公平嗎?
我也看到一些住在小寺廟的人,天天關門,沒有事情做,只有初一、十五開個門讓信徒進來燒個香,所收的香油錢,也夠他維持三餐生活了。但,我能做這樣的出家人嗎?這不就是如一九五二年時,印順法師在新竹「台灣佛教講習會」曾經對我說過的:「修行、修行,假藉這個名義說這句話的人,有時候看似好聽,其實是懶惰的代名詞。」我不能用修行的名義,剝削佛教的飯食,假藉修行的名義鬼混一生。我也不甘願那樣的醉生夢死。
生命意義 在於貢獻世間
我也在掛念,自己這一生怎麼樣度過?當然,我想到,生命存在的意義,不能離開大眾,不能離開對社會的貢獻,否則,只是做一個飯桶或者衣架?那有什麼價值呢?
那個時候,常有人問我有沒有灰心失志的時候,這我沒有感覺過,但前途茫茫不知道做什麼好,倒是經常有的念頭。尤其在台灣,寺院裡的廚房工作,大都由女眾負責,沒有一個青年和尚到廚房裡為大眾服務,為此,我不能做飯頭僧,就引為終身之憾了。其實,所謂修行,難道煮飯、燒菜不是修行嗎?那許多苦行的頭陀行者,不是修行嗎?大家不懂得生活中的修行,所以佛教才與社會脫節啊!
回想佛光山剛開山的時候,設備還非常簡陋,但已有不少《覺世旬刊》的讀者聞風而來,終於讓我有大顯身手的機會。那時,信徒都知道,來到山上如果找不到我,大概到廚房裡就可以看到我進進出出。有一年的春節,我在果樂齋炒麵,忙得不亦樂乎,曾有過一個中午就炒了二十鍋麵的紀錄。弟子們也才感覺到,除了做木工、水泥工之外,原來他們的師父也可以下得一碗好麵、煮得一盤好菜,而對我讚不絕口。在高雄市擔任救國團總幹事的張培耕就說過,吃過我煮的一碗麵,二十年都不能忘記。我也以此自豪,樂於典座煮飯供養大眾。
但是,命運沒有容許我有這樣的發心場所,還好,在典座之外,發現自己有另外一份能量:我可以寫文章。
雖然早期台灣的環境困難,為《人生》、《菩提樹》、《覺生》等佛教雜誌寫稿,大多沒有提供稿費,但我仍不斷供應文章給他們刊登。我甚至甘願不要稿費,也不願替社會那許多提供稿費的雜誌、期刊寫文章。因為我覺得我的生命是為佛教而生的,應該為佛教而做,我應該看佛教,不要去看社會的金銀財富。
儘管有佛教雜誌沒有提供稿費,但我仍筆耕不輟。記不清是哪一個出版社徵稿,我寫了一篇文章,還得到一百五十塊獎金;在台灣五○年代,物資普遍缺乏的社會,我非常高興的用這筆錢買了一本《辭海》,並且在第一頁寫上:「這本無言的老師,將伴著我度過未來無數的歲月,讓我見識天下,甚至可以起飛。」我感到自己非常的幸運,除了做工、做飯食以外,又添了一項能為佛教貢獻的地方,那就是可以用寫文章來護持佛法、弘揚佛法。
在我二十四、五歲的時候,《釋迦牟尼佛傳》、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》、《無聲息的歌唱》、《玉琳國師》、《十大弟子傳》、《八大人覺經講話》等,儘管沒有相關的參考書,卻也一本一本的陸續完成了。那許多小書,現在回想起來,自己都感到不成熟而不敢翻閱;徒眾卻告訴我,有些教授學者還把這些早期的寫作內容拿來做文學的研究。說來慚愧,這許多習作,實在不登大雅之堂;不過,當我知道這許多書籍以數萬本,甚至百萬本以上的數量流通時,我才稍微自我安慰:這不也是弘揚佛法?不就是「佛教靠我」嗎?
以無為有 發心無限無盡
現在,到了這種高齡,一生自稱「貧僧」的我,雖然建了幾百間的寺院、數十所大學、中學、小學、幼稚園、中華學校等等,但那都不是我的,這許多都是社會大眾的,都是佛教護法信徒的,我貧僧的性格,一生沒有改過。這也不是天生的,說來應該是要感謝慈悲的師父給予我良好的教育。在大陸,我跟隨他十多年,不曾給我一件衣服、不曾給我一塊錢,也不准我出外參學,出家做和尚,日子比在家裡的生活還要窮苦。
有那樣一個威風的大和尚做師父,怎麼自己這樣的寒酸?但現在才感受到,慈悲偉大的恩師,他養成我後來的人生沒有購買的習慣,沒有對物質的欲望。因此,我經常講「以無為有」的觀念。無,不是沒有,你懂得以後,「無」的裡面,只要有發心,它是無窮無盡、無限無量的。
從此以後,我講經說法,推動念佛會,推動鄉村教育,推動兒童教育、藝文寫作,為青年人辦補習班,為老年人組織念佛道場……,我覺得這樣去做,大概我這一生就不會做「吃教」的人了。
到了這個時候,也有很多的青年來包圍我,表示要跟隨我學佛出家。起初也是不得已,他們在沒有得到我的允許下就自行落髮,我不得不為他們辦一個小型的佛教學院。後來,一年一年招生,學生一年一年的增加,一不做、二不休,就從高雄壽山寺到滿山麻竹的佛光山開山了。
(上)
- 支持福報,做別人生命中的貴人 -
前往支持